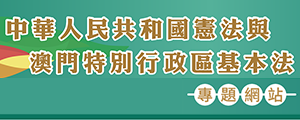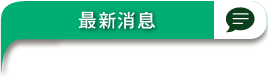
尊敬的鄭若驊司長、賈桂德司長、曾祥陸廳長,
尊敬的黃進會長、王振民會長,
各位專家學者、各位嘉賓,
早上好!
感謝各位領導、各位嘉賓對澳門回歸20週年對外法律事務研討會及圖片展的大力支持和協助。20週年是回顧過去、展望未來的日子,藉此機會,我想就澳門處理對外法律事務相關問題分享我的一些看法和體會,我的發言以三個關鍵詞為主題:成績、經驗和展望。
第一個關鍵詞是:成績。
回歸20年來,在中央政府的指導和支持下,澳門嚴格依照《憲法》和《澳門基本法》辦事,在處理對外法律事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績,舉其要者,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:
一,適用多邊條約數量屢創新高。在澳門回歸的過渡期間,中葡兩國就多邊條約適用澳門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磋商。澳門回歸時,共適用了158項多邊條約。這些條約在澳門的適用,是在“一國兩制”方針指導下創造性運用國際法的結果,為澳門維持繁榮穩定創造了有利條件。澳門回歸後,適用多邊條約的腳步在國家的支持下,進一步加快。截至目前,適用特區的條約已經超過600項,涉及外交國防、人權、民航、知識產權等17個領域。透過適用這些條約,特區參與相關多邊國際事務的權力得到制度性保障。
二,談判簽署大量雙邊合作協定。根據《澳門基本法》的規定,特區可在經濟、貿易、金融等領域以“中國澳門”名義,單獨同世界各國、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,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。《澳門基本法》還規定特區可根據中央政府的具體授權,簽署司法互助協定、互免簽證協定、民航協定。可以說,《澳門基本法》在涉外方面賦予特區非常廣泛的權力,這種安排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少見的。回歸以來,特區為拓展對外合作關係,在上述領域簽署了110多個雙邊合作協議。例如,在2019年,特區就與葡萄牙、蒙古、韓國等國簽署了4個司法互助協定,成為特區成立以來簽署司法互助協定最多的年份。在其他領域,特區與阿根廷簽署了《互免簽證協定》,與國際組織颱風委員會秘書處簽署了《行政、財務及相關安排的協定》等。這些雙邊協定為特區開展對外交往合作提供了堅實的支撐。
三,深度參與各領域國際會議。回歸前,由於多方面的原因,澳門參與國際會議的機會很少,經驗也不多。回歸後,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特區廣泛參與國際經貿、金融、稅務、旅遊、打擊犯罪、反洗錢、國際私法等各領域的國際會議,並在很多議題上積極參與討論磋商,不但拓寬了特區的國際視野,也提升了國際知名度和特區人員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。例如,今年3月,特區參加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核可中國第三輪國別人權審議報告,我本人擔任中國代表團其中一位副團長。特區參會反響很好,既展現了“一國兩制”的優勢,也宣傳了特區在保護人權方面的新進展;今年10月,亞太區打擊清洗黑錢組織(APG)正式發佈報告,澳門成為全球首個反清洗黑錢國際標準法律技術合規的會員。此外,一些國際會議在澳門成功召開,中國-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、颱風委員會等國際組織還在澳門落戶。20年來,特區從參加國際會議的“生手”成長為“多面手”,從制定國際規則的旁觀者轉變為積極參與者和貢獻者。
四,積極構建特區涉外法律制度體系。回歸前,澳門在涉外領域少有專門立法。回歸後,特區為落實《澳門基本法》的規定,從實際需要出發,制定了多個法律法規。例如,為給特區對外開展刑事司法互助提供法律依據,制定了《刑事司法互助法》和《司法互助請求的通報程序法》;為及時有效落實聯合國制裁決議和相關國際公約規定的制裁義務,特區制定了《關於遵守若干國際法文書的法律》。在工作機制方面,通過頒布行政長官批示,設立直屬於行政長官的司法互助工作小組,由行政法務司司長協調。通過20年的不懈努力,特區涉外法律制度體系已經比較完備,為處理對外事務提供了規範和指引,也有利於從制度層面落實“一國兩制”和《澳門基本法》。
綜上所述,澳門回歸20年來,在對外法律事務方面積極探索,取得了豐碩成果,不僅為特區的繁榮穩定創造了條件,也為“一國兩制”行穩致遠提供了堅實的支撐。20年在對外法律領域的成功實踐,從一個很好的角度充分說明,“一國兩制”是“行得通、辦得到,得人心”的。
第二個關鍵詞是:經驗。
20年的成功實踐來之不易,其中有一些好的經驗值得我們認真總結,繼續堅持並不斷發揚下去,從而進一步做好將來的工作。
一,堅守“一國”之本,善用“兩制”之利。在處理涉外法律事務過程中,特區始終牢牢堅持“一國”原則,切實維護國家統一、主權、領土完整,以及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。在堅持“一國”原則的基礎上,我們充分發揮特區作為一個單獨司法管轄區的獨特優勢,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根據特區需要做出特殊安排。事實證明,“一國”原則堅持得越好,“兩制”的便利就發揮得越好,這是一個良性互動、相互促進的過程。例如,在適用條約時,凡是涉及外交、國防等中央事權的,特區政府都與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;凡涉及特區自治領域的,特區根據實際需要提出適用或不適用的建議,包括做出與中央政府不同的聲明和保留,中央政府從來都予以尊重。20年來,從沒發生中央政府不考慮特區的建議或不與特區政府溝通,就否定特區政府建議的情況。
二,切實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,充分行使特區高度自治權。為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,特區政府主要有兩方面的做法:一是制定相關立法,使《澳門基本法》中規定的中央權力能夠在特區落地。例如,特區通過制定《司法互助請求的通報程序法》等法律,規定特區在處理司法互助請求時必須及時向中央政府通報,“如中央政府基於國防、外交、國家的主權、安全或公共秩序,對提出或接受某項司法互助請求發出指令並書面知會行政長官,行政長官須根據指令的內容作出相應批示”。二是與中央政府建立相關工作機制。例如,我們建立了適用條約工作機制、商簽雙邊協定請求授權機制等,將工作程序規範化,使中央政府的關切能夠通過制度化途徑得到解決。與此同時,特區積極充分行使高度自治權,在《澳門基本法》規定的自治領域廣泛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開展合作,簽署並實施合作協議,中央政府一貫充分尊重,並積極給予協助。例如,由於特區體量小,在對外交往過程中,一些建議有時得不到外方的積極回應,當特區請求中央政府協助時,中央政府總是利用外交資源給予大力協助,積極促成。
三,加強交流借鑒,提升法治水平。特區是外向型經濟體,必須建立國際化、法治化營商環境。特區成立以來,我們通過參與涉外法律事務,與各方開展廣泛交流,積極吸收國際通行規則,借鑒最佳實踐,使特區的相關法律制度與國際接軌,實現了本地法與國際法的和諧互動。在適用多邊條約時,特區政府會檢視現有法律,盡可能避免本地法與條約的衝突,並彌補可能存在的法律空白,根據需要制定新法律或對現有法律進行修改,確保特區能夠切實履行條約義務。一些條約特別是人權條約規定了履約監督機制,對於監督機制向澳門提出的合理建議,特區總是認真對待,凡是可以採納的都盡量採納,不斷改進自身工作。特區對參與涉外法律事務採取積極嚴肅的態度,既展現了良好的國際形象,也有力配合了特區法律改革進程,提升了自身法治水準。
四,積極面對挑戰,不斷開拓創新。“一國兩制”作為一項新生事物,一直在實踐中不斷探索、開拓前進,特區涉外法律事務也不例外。特區成立以來,在涉外法律領域不斷遇到新問題、新挑戰,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協助下,特區政府積極面對,妥善解決。回歸初期,特區涉外立法不足,我們推出多部法律法規,重點做好“建章立制”;2006年和2010年,針對《澳門基本法》對多邊條約和雙邊條約適用特區的程序規定過於原則的問題,特區與中央政府密切配合,建立了規範的工作機制;針對特區履約報告收集資料難等問題,特區政府規範工作程序,加強內部協調,確保履約報告全面準確;針對特區政府國際法人才不足問題,我們商外交部建立了國際法培訓項目,受到各單位歡迎;近年來,為解決司法互助協定數量不足問題,我們多管齊下,制定詳細的工作規劃,並與外交部駐澳公署聯合舉辦“周邊國家司法執法高級官員參訪活動”,推動有關國家與特區商簽司法互助協定,取得顯著成效。面對困難和挑戰,只要加強與中央政府的溝通,加強特區相關部門的內部協調,廣泛聽取理論界的意見和建議,就一定能找到適當的解決辦法。
第三個關鍵詞是:展望。
過去20年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,但是我們不能自滿,要清醒地認識到內外形勢的變化對特區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,要看到已經做的工作還不能完全滿足特區進一步發展的需要。展望未來,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特區對外法律工作。
一,加強研究和宣介。20年來,對“一國兩制”和《澳門基本法》的研究總體來說不斷走向深入,但毋庸諱言,對一些重要涉外法律問題的研究還比較薄弱,對實踐中新出現問題的關注和研究也不夠及時。例如,特區如何處理國際條約與本地法關係問題、中央政府締結的雙邊協定適用特區問題、區際司法協助涉及的國際法問題,大灣區建設涉及的國際法問題,等等。此外,雖然特區涉外法律實踐非常成功,但對國際社會的宣介還不夠,也不系統。因此,理論界和實務界要攜起手來,加強對有關問題的研究和探索,多出高水準的理論成果,同時要善於利用國際平臺對外宣介,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全面準確了解“一國兩制”。
二,加快談判雙邊協定。特區雖然已經締結不少雙邊協定,但在部分領域締結的協定數量還比較少,例如投資保護領域。特區正大力推進“一中心、一平臺”建設,並深度參與“一帶一路”倡議,這要求特區必須加大投入,在有關領域加快商簽雙邊協定,為開展對外合作提供機制化保障。在司法互助領域,目前特區正與10個國家談判相關協定,並向另外5個國家提出了談判建議。
三,加強內部機制和能力建設。由於涉外法律事務的獨特屬性,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進行集中統一管理,例如協定內容統一審批、協定正本集中保存等。特區目前對涉外法律事務的管理,總體上還屬於分散管理模式,未來可積極探討加強集中統一管理。另外,特區各部門從事涉外法律事務的人員還不多,要進一步加強人員培訓,建設一支高素質、複合型的工作團隊。
四,加強主動塑造。特區在參與和處理對外法律事務方面已經積累了一定經驗,有條件更加積極主動地開展未來的工作。例如,在適用國際條約方面,可以在中央政府徵求特區政府意見之前就開展研究和準備工作,避免倉促;在參與國際會議和談判方面,要從國家和特區的實際需要出發,積極研究問題,多提有分量的意見和建議,貢獻“澳門智慧”,在談判過程中也可以承擔更重要的角色,配合國家外交大局。
各位領導、各位嘉賓:
澳門曾在中國的對外事務中扮演了獨特角色。萬曆三十六年(1608年),香山知縣頒布《制澳十則》,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單行涉外行政管理法規。萬曆四十二年(1614年),廣東海道副使制定《海道禁約》,這是明朝政府管理澳門涉外事務最重要的地方法規。乾隆九年(1744年)和十四年(1749年),澳門同知先後頒行《管理番舶及澳夷章程》和《澳夷善後事宜條議》,這是清政府為加強澳門通商和在澳外國人管理制定的兩個單行條例。但在鴉片戰爭後,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,逐步喪失了對澳門的治理權,其標誌是1887年的中葡《北京條約》。新中國成立後,中國政府從歷史和現實出發,逐步醞釀並提出“一國兩制”方針,並於1987年與葡方簽署聯合聲明,為最終和平解決澳門問題鋪平了道路。歷史是最好的老師。針對積貧積弱的舊中國,“澳門之子”鄭觀應在《盛世危言》中指出,“(國際)公法仍憑虛理,強者可執其法以繩人,弱者必不免隱忍而受屈也。是故有國者,惟有發憤自強,方可得公法之益。倘積弱不振,雖有百公法何補哉?”如今,我國已經進入新時代,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民族復興的目標,我們要抓住歷史機遇,充分發揮澳門的獨特優勢,實現澳門可持續發展,續寫“一國兩制”的新輝煌。
最後預祝研討會和圖片展取得圓滿成功。